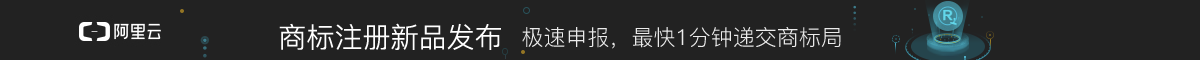萧统(501年―531年5月7日),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祖籍江苏武进)人。南朝梁代文学家,梁武帝萧衍长子,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长兄,母为丁贵嫔(丁令光)。
 天监元年(502年)十一月,萧统被立为太子,然英年早逝,未及即位即于中大通三年(531年)去世,谥号“昭明”,葬安宁陵,故后世称其为“昭明太子”。天正元年(551年),侯景立豫章王萧栋即位,追尊萧统为昭明皇帝。大定元年(555年),其子萧詧建立西梁,又追尊萧统为昭明皇帝,庙号高宗 。曾主持编撰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汉族诗文总集《文选》(又称《昭明文选》)。
天监元年(502年)十一月,萧统被立为太子,然英年早逝,未及即位即于中大通三年(531年)去世,谥号“昭明”,葬安宁陵,故后世称其为“昭明太子”。天正元年(551年),侯景立豫章王萧栋即位,追尊萧统为昭明皇帝。大定元年(555年),其子萧詧建立西梁,又追尊萧统为昭明皇帝,庙号高宗 。曾主持编撰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汉族诗文总集《文选》(又称《昭明文选》)。
昭明太子做太子29年,仅次于清太子爱新觉罗·胤礽和汉武帝卫太子刘据。
清太子爱新觉罗·胤礽(1674-1725年),乳名保成,清圣祖玄烨第七子,母为仁孝皇后赫舍里氏。除康熙早殇诸皇子外序齿为皇次子。因其胞兄、嫡长子承祜幼殇,故在胤礽刚满周岁时即被确立为皇太子。他是清代历史上唯一一位、也是中国官方正史上最后一位明立皇太子。
 幼聪慧好学,文武兼备,代为祭祀、监国,颇具令名,康熙帝对皇太子最为重视与宠爱,却因教子失当、兼之康熙朝后期党争纷乱,致太子人格分裂,历经两立两废,终以幽死禁宫收场,被追封为亲王。康熙十四年十二月立为皇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一废,共33年,加上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到康熙五十年再次被废2年,总共是33+2=35年。
幼聪慧好学,文武兼备,代为祭祀、监国,颇具令名,康熙帝对皇太子最为重视与宠爱,却因教子失当、兼之康熙朝后期党争纷乱,致太子人格分裂,历经两立两废,终以幽死禁宫收场,被追封为亲王。康熙十四年十二月立为皇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一废,共33年,加上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到康熙五十年再次被废2年,总共是33+2=35年。
 卫太子刘据(前128年-前91年),汉武帝刘彻嫡长子,汉昭帝刘弗陵异母兄。
卫太子刘据(前128年-前91年),汉武帝刘彻嫡长子,汉昭帝刘弗陵异母兄。
母为卫皇后。刘据生于元朔元年(前128年)春,于元狩元年(前122年)夏立为皇太子。刘据成年后,汉武帝每每巡游天下,便以国事交付太子刘据。太子为政宽厚,屡屡平反冤案,深得民心。征和二年(前91年),刘据在巫蛊之祸中被江充、韩说等人诬陷,因不能自明而起兵反抗诛杀江充等人,汉武帝误信谎情,以为太子刘据谋反,遂发兵镇压,刘据兵败逃亡,最终因拒绝被捕受辱而自杀。
 元狩元年获立为皇太子,征和二年(前91年)被杀,总共是32年。不过后来孙子刘病已当了皇帝,泉下安慰了。
元狩元年获立为皇太子,征和二年(前91年)被杀,总共是32年。不过后来孙子刘病已当了皇帝,泉下安慰了。
昭明太子萧统尊宠地位,文学编纂家的阔大胸襟,加之“美姿貌,善举止”的风雅气度,使得昭明太子成为历史夜空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人们在欣赏明珠光芒的同时,却常常忽略了那酝酿明珠的蚌的痛苦。
昭明太子的一生,可谓至善至美。他聪颖好学、博古通今、孝顺父母、宽政爱民。 昭明太子聪明早慧,读书过目不忘。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八岁“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 昭明太子天性仁爱,又加上熟读经书,研习佛经,他能够切身体会民间疾苦,竭尽所能帮助百姓。普通年间,梁军北伐,京城米价暴涨,昭明太子便下令宫中节衣缩食,赈济百姓。每逢雨雪绵绵之际,照明太子都要派人仔细体察民情,遇到困窘之人,便拿米和衣物接济他们。对于罪犯,他也要求从轻发落。
 这样的储君,无疑将是梁朝的大幸,是百姓的大幸。 然而,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使得昭明太子成为一具澄明的偶像,不能有一点儿瑕疵,否则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从高高的圣坛跌下,摔得粉身碎骨。昭明是太子,更是人,他尽可能地臻于完美,但他也越来越感到肩头担子的重量,他知道,终有一天,那担子会像泰山压顶一样,将他永远地压在下面,他不敢想象下去……
这样的储君,无疑将是梁朝的大幸,是百姓的大幸。 然而,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使得昭明太子成为一具澄明的偶像,不能有一点儿瑕疵,否则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从高高的圣坛跌下,摔得粉身碎骨。昭明是太子,更是人,他尽可能地臻于完美,但他也越来越感到肩头担子的重量,他知道,终有一天,那担子会像泰山压顶一样,将他永远地压在下面,他不敢想象下去……
 在《梁书》中,昭明像圣人,通体光明,彪炳千秋,我们找不到一丝烟火气息。倒是在《南史》中,我们终于看到一片祥和中的一朵小小的乌云,这朵乌云迅即幻化为昭明头顶的利剑。 那就是蜡鹅厌祷事件。这宫廷之争中频频上演的悲剧,居然又一次拉开了帷幕,而主角就是昭明太子。 丁贵嫔去世时,昭明已为母亲选好了墓地,但宦官俞三副因受另一卖地人贿赂,以昭明所选墓地对武帝不吉利为由,劝武帝更换。晚年迷信的武帝自然听信了其佞言妄语,将丁贵嫔葬于俞三副推荐的“风水宝地”。
在《梁书》中,昭明像圣人,通体光明,彪炳千秋,我们找不到一丝烟火气息。倒是在《南史》中,我们终于看到一片祥和中的一朵小小的乌云,这朵乌云迅即幻化为昭明头顶的利剑。 那就是蜡鹅厌祷事件。这宫廷之争中频频上演的悲剧,居然又一次拉开了帷幕,而主角就是昭明太子。 丁贵嫔去世时,昭明已为母亲选好了墓地,但宦官俞三副因受另一卖地人贿赂,以昭明所选墓地对武帝不吉利为由,劝武帝更换。晚年迷信的武帝自然听信了其佞言妄语,将丁贵嫔葬于俞三副推荐的“风水宝地”。
 但此时,另一位道士也胡言乱语,他对昭明说,俞三副所选墓不利于太子,如果将蜡鹅及诸物埋在墓侧的太子位,便能逃过此劫。昭明自然照办-他在最不该犯错的时候犯下了大错。武帝得知后,大为震惊,认为此举当属忤逆,从此对昭明心存芥蒂。昭明大悔,以他的纯孝,竟当此恶名,他无法辩解,更无法排遣,唯有忧伤以终老。
但此时,另一位道士也胡言乱语,他对昭明说,俞三副所选墓不利于太子,如果将蜡鹅及诸物埋在墓侧的太子位,便能逃过此劫。昭明自然照办-他在最不该犯错的时候犯下了大错。武帝得知后,大为震惊,认为此举当属忤逆,从此对昭明心存芥蒂。昭明大悔,以他的纯孝,竟当此恶名,他无法辩解,更无法排遣,唯有忧伤以终老。
在一个阳春三月,昭明太子和姬妾一起荡舟采荷,坠水感病,一个月后,郁郁而终。《昭明文选》里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涉江采芙蓉》,那朵纯洁的莲花,不知他采之欲遗谁,是远道的恋人,还是忧伤的自己?但他终于自由了,连他的死法都这么唯美。 昭明死于自己的优秀,如此优秀的人,是不会,也不应当犯错的。他的父亲不允许,他自己也不允许。理解他的唯有那朵将他引度的莲花,它知道他曾经怎样深陷在污泥里,而现在又是怎样的洁净无尘。
 传统史学界称萧统英年早逝为“受人诬害至死”。《资治通鉴》亦将责任推于服侍太子之宫监鲍邈。然窃以之为非。何哉?其根本之原因在以萧统之贤而有才,已威胁其父萧衍之威望和统治基础。萧衍虽以多次“出家”而向天下诏告自己“不恋权力”、“一心向善”,但一旦自己的亲生儿子有可能挑战自己的“权威”时,便丑态毕露,穷凶极恶地向儿子兴师问罪,可见权力毒药之深而烈。然而后世所悲者,一为梁失明君,是以梁祚于武帝饿死台城之后不久即告消亡,江南人民行将再一次陷入万劫不复之战乱与改朝换代的无所适从之中;二为萧统早亡,中华民族失却了一个文化再造的良好机会。
传统史学界称萧统英年早逝为“受人诬害至死”。《资治通鉴》亦将责任推于服侍太子之宫监鲍邈。然窃以之为非。何哉?其根本之原因在以萧统之贤而有才,已威胁其父萧衍之威望和统治基础。萧衍虽以多次“出家”而向天下诏告自己“不恋权力”、“一心向善”,但一旦自己的亲生儿子有可能挑战自己的“权威”时,便丑态毕露,穷凶极恶地向儿子兴师问罪,可见权力毒药之深而烈。然而后世所悲者,一为梁失明君,是以梁祚于武帝饿死台城之后不久即告消亡,江南人民行将再一次陷入万劫不复之战乱与改朝换代的无所适从之中;二为萧统早亡,中华民族失却了一个文化再造的良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