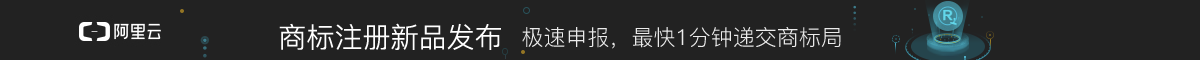雍正三年八月一天深夜,养心殿的御案上摆放了两道六百里加急奏折,一份是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另一份是云贵总督杨名时的。雍正知道,在这两个奏折的背后,延伸出帝国未来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以杨名时、查弼纳、裴度、张楷等为代表的保守派;一条是以田文镜、李卫、杨文乾等为代表的改革派。
 田文镜和李卫是雍正朝的红人,大家都很熟悉,因此就不多介绍了。而杨名时同样是当时名扬天下的封疆大吏,他是人人称道的“清官”,这位雍正年间的旷世大儒,是被天下学子朝拜的理学领袖。年轻治学时,在酷热的三伏天里他仍手不释卷,以至于身上的白衣被汗渍染成浅皂色。
田文镜和李卫是雍正朝的红人,大家都很熟悉,因此就不多介绍了。而杨名时同样是当时名扬天下的封疆大吏,他是人人称道的“清官”,这位雍正年间的旷世大儒,是被天下学子朝拜的理学领袖。年轻治学时,在酷热的三伏天里他仍手不释卷,以至于身上的白衣被汗渍染成浅皂色。
在云南任职期间,杨名时还千方百计地革除雍正“摊丁入亩”等政策的内在弊端,实实在在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云南一度水患,百姓流离失所。杨名时绞尽脑汁,从盐商那里借了银两,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雍正帝的理政风格是雷厉风行,而杨名时的风格则是春雨润物。雍正刚劲的政令每每到了杨名时的辖区就会被分解、柔化,杨名时却因此得到了百姓的赞誉。
 在民间自古就崇尚清官,从包拯到海瑞,百姓们在心里头一直描绘着一位操守廉洁、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完美形象;在知识分子心里头,从颜回到朱熹,士人们有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
在民间自古就崇尚清官,从包拯到海瑞,百姓们在心里头一直描绘着一位操守廉洁、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完美形象;在知识分子心里头,从颜回到朱熹,士人们有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
当雍正看到田文镜和杨名时的奏折后,深深陷入沉思,一个月后,雍正重新调整朝纲,希望为大清后二百年的吏治奠基。他发表了长篇谕旨,把保守派与改革派的督抚们列出名单,赞扬田文镜为首的“能臣”,攻击杨名时为首的“清官”。
杨名时在云南从政七年,仅参劾过一位进士出身的知县,这正好成为雍正的靶子。雍正曾表示:“那些封疆大吏为了图宽大仁慈之名,沽去安静之誉,对贪官庇护之,对强绅宽假之,对地棍土豪则姑容之,对巨盗积贼则疏纵之,这样会使天下百姓暗中受其荼毒,无可控诉。”雍正把杨名时等五位保守派督抚,看成是孔子口中的“乡愿”,即“德之贼也”。
 五位被批判的督抚中,只有杨名时一人还击了。他上书雍正帝,用周密的理学思维,旁敲侧击地批评了雍正推崇的田文镜、李卫等“能臣”。自此,雍正与杨名时的辩论升格为路线斗争。朝廷中众多朝臣还没有意识到,这次辩论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前,政府关于执政方针最典型的一次辩论。
五位被批判的督抚中,只有杨名时一人还击了。他上书雍正帝,用周密的理学思维,旁敲侧击地批评了雍正推崇的田文镜、李卫等“能臣”。自此,雍正与杨名时的辩论升格为路线斗争。朝廷中众多朝臣还没有意识到,这次辩论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前,政府关于执政方针最典型的一次辩论。
雍正想撕破杨名时的理学伪装,把他代表的名儒集团彻底妖魔化。就在这个当口,曾任云南布政使的李卫呈上一个奏折,罗织出杨名时的“四大罪状”。雍正马上选派钦差大臣朱纲南下云南,务必扒下杨名时假道学的画皮。
 贪功心切的朱纲很快发现,这“四大罪状”纯属子虚乌有,当雍正降旨要杨名时供认“巧诈居心”时,杨名时宁死不屈。朱纲欲用刑讯逼供,新继任的云贵总督鄂尔泰斥责朱纲说:“你见过岳飞雕像前跪了几百年的秦桧吗?”
贪功心切的朱纲很快发现,这“四大罪状”纯属子虚乌有,当雍正降旨要杨名时供认“巧诈居心”时,杨名时宁死不屈。朱纲欲用刑讯逼供,新继任的云贵总督鄂尔泰斥责朱纲说:“你见过岳飞雕像前跪了几百年的秦桧吗?”
此时,雍正操纵的杨名时案迷失了方向。如果因为几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杀死杨名时,有失帝王的风度与襟怀,更为成全杨名时“清廉而终”的大儒名望;如果继续审讯羞辱,却也不能摧毁杨名时坚守的道德底线,而且还会牵扯出李卫、原云贵总督高其倬等宠臣的一连串贪污案。
最终,雍正意味深长地说:“杨名时一案,要等到云贵官僚的贪污案清结之后,再降谕旨。”在此案中杨名时虽然是获胜了,但他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终雍正一朝,一直戴罪云南,成为了一介布衣。
 乾隆即位后,这位被雍正冤枉的封疆大吏终于苦尽甘来,以其诚朴端方被诏赴京,加礼部尚书衔兼国子监祭酒,并兼值上书房南书房。乾隆二年(1737年)杨名时病故,赠太子太傅,入贤良祠,赐谥文定。
乾隆即位后,这位被雍正冤枉的封疆大吏终于苦尽甘来,以其诚朴端方被诏赴京,加礼部尚书衔兼国子监祭酒,并兼值上书房南书房。乾隆二年(1737年)杨名时病故,赠太子太傅,入贤良祠,赐谥文定。